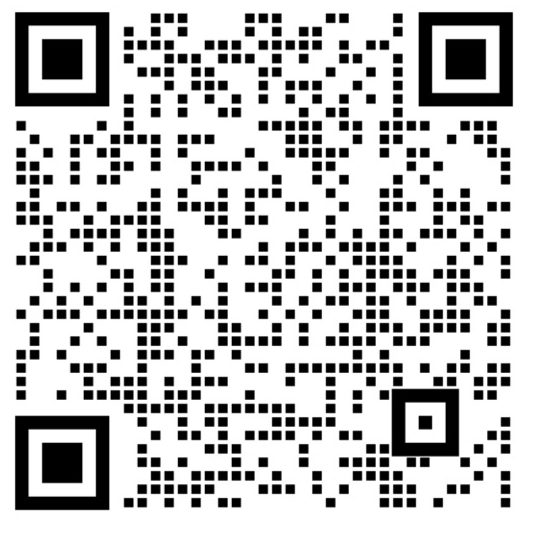我國傳統論的這種偏重人文藝術而疏忽自然百科、系統單一而非多元的傾向,導致其理論系統極大局限性,對于應用翻譯這一專門領域,更是缺乏應有的重視。“案本”、“求信”過于注重原文形式,往往導致直譯甚至硬譯;“神似”、“化境”追求“神韻”、“意境”,在很大程度上也只能在文學翻譯中大顯身手,對客觀性應用性強、靈活性多樣性突出的應用翻譯,似乎鮮有用武之地。上海法語翻譯認為在翻譯策略上,過去一般以討論全譯為主。而應用翻譯傳遞信息往往是有限制性的;或綜合地、或概要性地或部分傳遞。一句話,怎么譯,要以翻譯委托人的目的為準。應用翻譯,無論是在譯法上,還是譯品形式上,可變性更大”(方夢之,2003)。不同文本的功能和目的不一樣,上海翻譯中心翻譯的要求和標準也不一樣,例如,商貿公文有商貿公文的規范和格式,廣告宣傳有廣告宣傳的形式和習慣,時政科技文章又有時政科技文章的原則和要求,上海翻譯中心各自采取的翻譯策略自然不會一樣,絕不是一個“求信”或“神似”能解決得了的問題。同時,應用翻譯信息性、勸導性和匿名性的特點也要求譯者在翻譯中,更多考慮如何使譯文傳遞的信息便于讀者理解和接受,如何有效地實現譯文預期的功能和目的,原文的形式和內容往往要服從于譯文的需要,服從于文本的交際功能。因而,上海翻譯中心必須根據譯語的文本規范和讀者樂于接受的形式對原文作些調整和修改:或抽象概括原文信息改換原文形式,或增刪補改原文內容進行篇章整合,甚至將翻譯變成寫作,把原文改得面目全非,這些做法在應用翻譯中是常有的事,哪一條都不符合傳統譯論的標準,卻都是應用翻譯行之有效的慣用方式。從解決應用翻譯理論的實際出發,不妨環顧一下西方的現代翻譯理論。